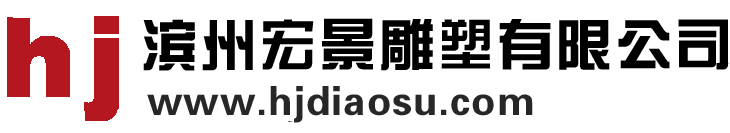芒克:2004年初,我的一個朋友給我買了一些顏料和畫布,建議我可以畫畫,我就直接上手了。我也就是瞎畫,現在也還是瞎畫。我以前對繪畫沒興趣,也從來沒有訓練過。有點荒誕的是,我自2004年初開始畫畫,年底就辦了展覽,還被人買走了。所以從2004年起,我算是把畫畫當成了一份正式職業,一門手藝,有自己的經紀人,有自己的畫室,每年完成20多幅作品,我就靠這個養家糊口。我這個詩人現在就靠畫畫吃飯。
早報:當年的很多詩人現在都去了高校,比如北島、西川、多多,您有這樣的機會嗎?
芒克:沒有大學邀請過我,大學請我演講我都拒絕了,我能講什么?我沒有太多的校園經歷,這輩子干得最長的工作就是在白洋淀插隊7年。我18歲去農村,回城后去工廠呆了1年多,后來因為辦雜志被開除,打那以后就沒有進過單位了。年輕的時候,胡來成了詩人,現在瞎畫成了畫家,好歹活到現在。我覺得挺好。你真叫我到單位,我也不習慣。這跟我性情有關,人各有命。現在帶孩子玩,習慣了,挺好。
“那時候,我們一激動就扒火車”早報:能談談白洋淀插隊的7年嗎?
芒克:在農村我也不勞動,一年的工分居然倒欠。我整天在外邊玩,他們也不怎么管我。我在村里混得爛熟,跟玩伴們關系很好。現在,那個時候的玩伴居然都成了大人物,而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村子里的壞小子。以前我每年都回白洋淀,現在很少去了。幾年前,和我玩得最好的朋友死了,那天晚上我沒怎么睡,特別不舒服,就是覺得這地方不應該再來了。
早報:當時,寫詩意味著什么?芒克:那個時候寫詩是最簡單的事情,有筆和紙就可以了。寫詩就是沒事情干。在白洋淀,我們村和別的村的知青都在寫,但大家各寫各的,真正熱鬧還是在辦雜志的時候。年輕的時候寫詩,哪里想過會出名什么啊,只要別被抓起來就行。那個社會太無聊了,寫詩無非是想自由一些,別你們讓我們說什么,我們就得說什么。我們看點書接觸了點西方的東西,我們熱愛自由,所以在某種程度上,去農村也是一個好的事情。城里面管束得那么嚴酷,到了農村后發現,農民不是太關心“文革”。自己寫點東西,老百姓知道什么啊。那時候就是興趣,翻了點洋書就想要寫點什么,真沒想到還成了什么東西了。你問我這些詩怎么寫的,忘了,就像不是我寫的一樣。
早報:但當時大家用的詩歌語言已經非常獨特了。芒克:當時,詩的語言就是大家瞎琢磨出來的,也沒有太在意。這幫人也沒有經過什么訓練,能閱讀的東西也不是太多。反正就是感覺,這樣寫好,大家基本上還互相認同。
早報:在那個時候,您還學著《在路上》去流浪了一回。芒克:那是1972年,我和彭剛他們,這些人有畫畫、寫詩、做音樂的,對西方的東西也看了不少,然后我們就心血來潮地說:我們也先鋒派了。我們對先鋒的理解就是超前,然后很沖動地學著《在路上》上路了,沒幾天就被遣送回來了。當時,我倆身上就2塊錢。那個時候很天真,對外省一無所知。那時候,我們一激動就扒火車,一路居然都沒有被查,直到漢口才查到我們逃票。然后我們又扒火車往回跑,在信陽的時候又被趕下來。我們實在沒轍,找誰要飯啊,滿街都是要飯的。后來實在餓暈了,遇到一個民政局的好心人,她給了我們2塊錢買吃的,還讓我倆去民政局找她。彭剛編瞎話,說我們錢丟了什么的,其實我們哪來的錢啊。后來她打電話到我媽單位――北京阜新醫院,我媽說,“幾天沒見你去哪里了?”后來我們就上了火車回北京,在火車上又大吃大喝。
早報:對比現在安定的生活,30多年前的事情好像很遙遠了吧?芒克:真的是好遙遠的事情,而且覺得不是我的事情,這事是我經歷的嗎?有人問我,為什么不寫回憶錄,我覺得沒啥可以回憶的啊,我做夢都不懷舊。百無聊賴才去懷舊,再百無聊賴就喝酒去。
說說您的看法:(無須注冊)
共0條評論暫沒有評論。